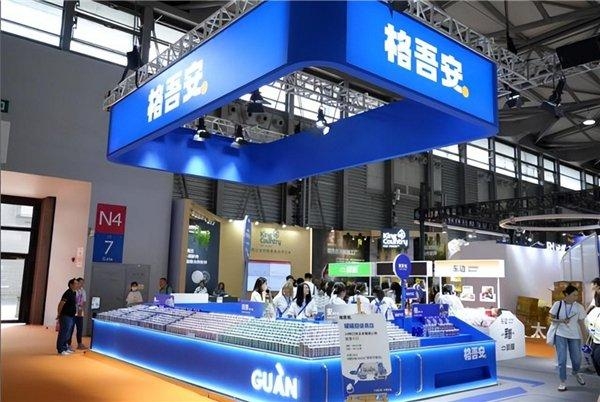他们几乎全年无休,随时待命。宠物不会和人约好时间走失。八年期间,他和团队找到的宠物大约一千多只。
“看见那边屋檐处凸出来的一小块儿了吗?”孙锦荣眼望着窗外,我顺着他右手指的方位也看了出去。
我并没有看到他所指的是什么。在我看来,远处的屋檐看起来都一个儿样。
“那是一只鸟。”他说。直到鸟儿飞走,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起飞的。
孙锦荣把这种一眼看上去和事物常态不一样情形的称作“异型”——在他给我举的这个例子里,异型就是“凸出来的一小块儿”,别的屋檐上没有。快速而精准地看到“异型”,是他职业的基础本领之一。
他是一名宠物侦探。
01每年,和几千只动物的交集
宠物侦探做什么?具体说来,就是受人雇佣,帮助寻找走失的宠物,通常是猫或者狗。寻宠过程中,需要使用的工具包括望远镜、夜视仪、强光手电筒、生命探测仪、管道探测仪等专业设备,而软件能力,则是宠物侦探的团队合作、经验程度、观察力等等。
在上海浦东郊区,39岁的孙锦荣租下一栋三层的民房,和十六个年轻人,以及他的老父亲住在一起。从独行侠一般做宠物侦探,到如今有所建树的小团队,他经历了八年。
几乎全年无休,随时待命。宠物不会和人约好时间走失。八年期间,他和团队找到的宠物大约一千多只。通常说来,白天找狗,夜里找猫,团队成员们几乎难以拥有正常的作息。
孙锦荣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。他说,这份工作让他脱发严重。疫情期间他不知觉胖了些,但这两个月,他又一下子瘦了十几斤。我见到他的时候,他看上去已经拥有正常偏瘦的体型。可他还想减到更轻的体重,因为更瘦才能“轻松地钻到车底盘下”。很多猫会躲到车底盘下。
孙锦荣自己有一套特殊的观察事物的方法。除了“异型”,他还从自己的工作里提炼出“色差”“动态”这两个概念。“再举个更生活化的例子。如果一桌子人围着吃饭,其中一个人是左撇子,这种情况也属于视觉上的‘异型’。我们做宠物侦探的,哪怕是无意识地扫一眼,也能一秒钟看到那个左撇子。”这种情况下,他看到的是事物排列状态的异常。
这些概念称不上严谨,但却实用,让他的徒弟们可以更加敏感地去从轮廓、颜色、活动等几个方面判断事物。“去注意一大片颜色中出现的不一样的颜色,因为那可能就是藏在绿叶中的动物,如果树叶有异常摆动,更要留意。”
这听起来有点玄乎,但他说平时就得从这些方面入手,长期培养自己的感官,到了寻找动物的现场,才能“像本能一样调动起来”。而这种敏感度,甚至不仅仅包括视觉——他需要感受风向,从纷杂的气味里识别出猫尿味儿,也要综合判断周围的环境,判断动物的去向。
这种寻找和接近动物的技巧,都是他花心思和时间总结出来的。此前,新京报曾报道,“为了模仿幼鸟的叫声来吸引猫,他练了两年多,终于能用嘴发出相似的声音。”
但所有的技巧、经验和直觉的运用,也同时需要放弃侥幸心态,否则就可能造成失误。“比如查看一段监控视频,需要把丢失时间前后几个小时一帧不漏地看完,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时间点里看到狗往左走,就兴冲冲往那个方向去找,但是它也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又往右走——监控还是录下来了,你没看到,就完全去了相反的方向。”
这有点近似于人们通常说的对“第六感”的运用——需要“笨功夫”,但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
猫会藏在人眼难寻的地方。比如楼顶房檐、下水道、灌木丛后……而无人机可以飞到高处,夜视仪方便在不惊扰动物的情况下进行夜间搜寻,生命探测仪则可把搜寻范围进一步缩小。这些硬件设备也像是他感官的延伸。
懂动物当然也是基本功了。比如,要给猫咪安全感,应该用毛巾或毯子盖上它们的眼睛。通常,这个团队还要向宠物主人详细了解它们各自的信息,包括年龄、性别、个性,以及它们熟悉的交流方式等等。
孙锦荣团队使用的设备
“一年要找多少只动物?”我想知道现在这个团队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。
他并没有精确计算过。不过他告诉我,“几千只是有的”。这几千只,包括一年接的全部寻宠订单数量,以及团队救助过的动物。前者是商业项目,后者是公益行为。救助,简而言之就是帮助流浪动物进入一个安全地带,这其中就包括帮困在高处的奶猫回到平地,帮流浪猫狗找到愿意收养的家庭,或联系治疗疾病的机构……如此种种。
十六个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,基本上是九零后、甚至九五后,有做过厨子的,有做过销售的,也有创过业的。孙锦荣给他们包吃住,底薪加提成,像带徒弟一样把寻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。
“法斗的市场价格很高,差不多一万以上一只,所以被人抱走的可能性很高。另外这种狗的鼻腔短,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也很热,要注意周围的水源,它可能会去寻水。”在一块白板上,孙锦荣画下了一幅简易地图,那是最近一只法国斗牛犬的走失地。“周围有菜市场,里面有卖卤菜熟食的,也要多注意这里有没有它的去向。”
他在地图上圈出了菜市场的位置,徒弟们点头记下。
孙锦荣正在给团队成员讲述寻宠的基本信息和经验
除了技术和经验,孙锦荣还希望这些年轻人能从这份工作里找到“价值感”,而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份工作。
“我觉得这工作能真的帮到人,也能帮到小动物。”金涛,一个皮肤白皙、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告诉我,这不是一份纯体力的劳动,得靠脑子。他通常在夜间寻猫,在这里待了快两个月,所以几乎没有晒黑的迹象。
金涛沟通能力强,所以也常常负责和失主的沟通。安抚失主的情绪,让对方冷静地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,在孙锦荣看来,也是这个职业的素养之一。除此之外,不轻言放弃、能吃苦、善于观察等等,也是他对徒弟的期望。“他们得在我这儿从男孩长成真正的男人。”
02职业寻宠第一人
这些经验都是孙锦荣拿脚走出来的。
二十多岁的时候,孙锦荣完全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做和宠物相关的行业。他在工厂打过工,后来和前妻一起开教育培训类的公司,甚至一度把业务做到了海外。在外人看来,那是他最“风光”的一段时光。
离异后,他选择净身出户,三十多岁的男人得从头开始一份事业,或者工作。朋友把他介绍到一个宠物救助机构,孙锦荣开启了一段此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——放弃企业主的身份,“收拾狗屎狗尿”。“那时候我就想放弃自己以前积累的全部自尊,把自己摁在地板上摩擦,摩掉我以前生意生涯中积累的虚荣。”
和动物打交道确实给了他不一样的体验。有一回,他随宠物救助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去菜市场救一只猫。他还记得见到那只猫的第一眼:沾满污泥的毛发令它无法把双眼睁开,看上去虚弱又无助。和他同行的人把猫一下子抱在怀里,用手挠着它的额头和下巴,毫无芥蒂。“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人能如此爱动物,一点儿也不嫌脏地爱它们。”
他们给猫洗了澡,猫变了个儿样。没了污泥,孙锦荣看到了一双“此生见过的最明亮的眼睛”。
从这一次起,他慢慢开始对动物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。救过的狗,在时隔半月后还会认得他、跟在他后边儿走。如今,当他找到丢失的宠物、帮助它们回家后,宠物在安全的环境里看他的眼神,是他在这份工作里最大的安慰——他在其中实现了某种帮助弱小的“侠义”情结。
从公开报道来看,孙锦荣是中国第一个以职业状态做寻宠的人。刚开始,他是个独行侠,没有助手, “一天就收个两三百劳务费,甚至有时一百块我也做,只想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来。”
“宠物侦探”这个名号是一个客户几年前给他的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叫自己正在干的事,“专业找狗的?听上去怪怪的”。
很难统计中国每年有多少只宠物走失,但在网络上,在小区的墙壁和电线杆上,人们多少都见过寻宠启示。一项美国的数据也许可以作为参考:全美平均有1/3的宠物会在生命周期内丢失,只有不到2%的猫和15%-20%的狗最终会被寻回。在孙锦荣接触的案例中,大多数宠物丢失都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:不拴狗绳、纱窗没关好、家门没关严实之类,他统称为“人祸”,或是“不当养宠”,属于本可避免的走失。
但是宠物能否找回,并不是一件能百分之百保证的事情。在走失期间,被人恶意占有、出车祸、死亡,或是主人本就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等等情况都可能发生。有人甚至打电话来,问孙锦荣能不能帮忙找找丢了两年的狗。
“这事儿和开锁、通下水道不一样,存在很多我们作为人都无法预料的认知盲点。”寻宠过程中要付出的精力和努力,可能大部分都属于“无用功”——因为无人拥有上帝视角,他们只能每一种可能性都试一试:从社区的监控摄像头,到挨家挨户地拿嘴问,甚至是翻围墙查看具体的环境……每一条路径只能提供一个视角的信息。
有一回,他们找一条牧羊犬,花了几天时间都没找到,最后费了很多力气摸排线索,才明白原来找错了地方。那条狗在高架桥上碰到了开窗键,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跳了出去,而当主人意识到狗丢了的时候,车已经开出去很远,所以给的地点信息也是错误的。直到找到狗,他们才把中间的线索给串起来,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。
有时候,宠物找到了,但却是死的,或是只能找到身体的一部分。前不久,孙锦荣的一个徒弟带回来一颗狗牙,那是他最后能找到的狗身的部分。最后,徒弟用透明的包装袋把那颗牙装好,寄给了狗主人——这让他对自己的培训成果倍感欣慰。“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个破布之类的,而是用干净的容器给它装好,这种基本的人道意识,也是我想传达给他们的。”
03难以算计的价格
孙锦荣需要面对许多不被理解的时刻。
孙锦荣做了八年,可大多数人对这个职业在做什么、怎么收费、如何评判服务成效,没有具体的认知或印象。有的失主对寻宠行动抱有过高的期望,甚至一个电话打过来就问“多少钱能找到一只狗”。“这不是一个付出了金钱和精力,就一定能有结果的事情。我们能做的,只是在受雇用的状态下,以我们的经验和技能,提高找到的概率。”
收费方式也是他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创造出来的。在谈好订单后,宠物失主需要先付一笔定金,这里面包括一些寻宠工作的基本成本,比如人员调配、寻宠启示打印、车辆的损耗等等。有时候,甚至寻宠的人已经到现场了,结果对方反悔,要求退还定金。“但有些人看不到已经付出的这些成本,他们只会看你有没有去找,甚至只看你有没有找到。”
不过近几年,这类事情渐渐少了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随着业务越做越大,他更能够挑选“能理解这件事”的、能理性沟通的人来作为他的服务对象。
我见到他的那天,正巧碰到他接了一通“不太愉快”的电话。他接了一个单子,期间也保持着和失主的联系。中途,一个电话打进来,对方对花钱寻狗这件事产生了犹豫——原来是失主的姐姐。这个家庭内部未对寻狗的决定达成一致意见,孙锦荣这边的人员却在第一时间就被调度到了现场,却因为这个家庭的迟疑,无法开展行动。
“我只对跟我下订单的人负责。”孙锦荣反复向对方强调。团队无法替任何失主做决定——这种情况下,只能等对方做好决定后,再采取下一步行动,别无他法。
中国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。《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显示,2019年中国城镇宠物-犬猫市场整体消费规模达2024亿元。艾媒咨询预计,2020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近3000亿元。
但是,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,职业寻宠也远没有形成行业规模。除了孙锦荣团队,人们很难在公共媒体上看到这群人的踪迹,也难以了解这类职业群体的生存状况。在日本,职业寻宠也是作为“新兴职业”存在,难以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。
也无法统计中国目前有多少人做着和孙锦荣类似的工作,但据锦荣说,“鱼龙混杂”。“全国真正在做这件事的团队不超过10家。另外有一些打着这个名号骗钱的,比如拿了定金就失联。”
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,孙锦荣也没有想过向社会募集捐款——尽管在一些人看来,他做的事情带有某种“公益色彩”。他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商业模式,让这件事情变得可持续。现在,他采取“劳务费+赏金”的收费方式,前者600~1800/天,依据寻宠出动的人数而定,后者3000元起,成功寻回才有这笔收入。如果没有找到,就只收取劳务费。这样算下来,可能一笔寻宠的费用就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只宠物的市场价格。
面对一些付不起价的失主,他也无能为力。“我希望人们能理性养宠,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养宠。”同时,为了呼吁人们避免宠物走失的“人祸”型悲剧,他通过自媒体和视频,向人科普科学养宠的知识。
在评价规则没有达成普遍共识、行业标准不明晰的情形下,上述“不理解”的情形出现也是自然。“其实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是,以靠纯赏金来养活团队——就是没找到的情况下,失主不用付出任何财力。但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规模,也需要我们团队有足够高的找回率。”目前,因为团队“每一天都要付出成本”,而赏金是无法覆盖这部分成本的。
他的父亲,也曾是不理解他的人。“老人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经的职业,劝我找个班上,好好稳定下来。” 但如今,见儿子的团队逐渐扩大,父亲有时帮衬着料理些家务,心也安了。
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个职业在做什么,他也开始做一些形象传播和运营。如今,他的团队还会把寻宠的过程剪辑成三分钟左右的视频,形式如同时下流行的vlog。在最新一期寻宠的视频中,他介绍了寻找一只猫咪的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。“寻找猫咪的过程中,我们常常要深入到动物的世界里,和蛇虫鼠蚁打交道已经习以为常。”在画面中,手电筒照着茂密的草丛,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工作要面临的日常环境。
随着名气的增大,媒体和拍摄团队也频频来访。然而,采访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工作,也可能让年轻人的虚荣心膨胀,他开始觉得“有些不好管理”,人员的流动性变高了。“有些年轻人在媒体上露脸之后,就不太用心工作了。”
但这可能本身就是职业化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。“一步一步来吧,先把该做的做好。”像解决其他的问题一样,他也只能面对,无法逃避。